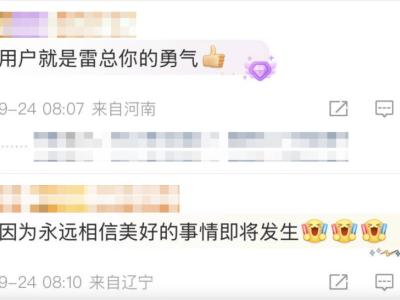在科技产品发布会上翻车,meta又一次成为舆论焦点。9月中旬的meta Connect年度开发者大会上,创始人扎克伯格亲自演示新款AI眼镜meta Ray-Ban Display时,遭遇了意想不到的尴尬。这款二代产品本应展现AI与硬件的深度融合,却在实时交互环节频繁卡顿,甚至在接听视频电话时因界面显示异常而失败。扎克伯格无奈自嘲:“开发多年技术,结果被WiFi拖了后腿。”但业内人士指出,问题远不止网络连接这么简单。

meta的困境并非个例。国内科技圈同样经历了一场“AI眼镜热”与“冷思考”的交替。今年6月,小米在“人车家全生态发布会”上推出AI眼镜,凭借雷军亲自带货的效应,产品上市前15天全网销量突破8万台,甚至传出内部将目标从30万台上调至50万台的传闻。然而,这股热潮很快退去。数据显示,8月中旬该产品在抖音的日销量从峰值5000-7500台暴跌至100-250台,线下门店的咨询量也大幅下降。一位小米之家店员透露:“现在一天可能只有一两个人问,试戴的更少。”
行业数据曾为AI眼镜描绘了一幅乐观图景。群智咨询预测,2025年全球市场规模将达570万台,同比增长110%,到2030年更有望突破1360万台。阿里也在7月宣布入局,推出首款自研AI眼镜“夸克AI眼镜”,采用双芯并行架构与双系统调度资源。但meta与小米的遭遇表明,技术验证期向商业分层阶段的过渡远比想象中艰难。
meta的新品问题集中在技术成熟度与市场定位的错位。其高端型号meta Ray-Ban Display虽在像素、防抖、续航上有所升级,但核心芯片仍与小米等国内厂商同款的骁龙AR1 Gen 1,未展现颠覆性突破。更争议的是,为追求“自然交互”,meta为眼镜配备了基于肌电图技术的神经腕带,用户需通过手部肌肉动作控制设备。这一设计虽减少“掏手机”的步骤,却被从业者批评为“画蛇添足”。“AI眼镜的核心是便捷,增加配件反而违背初衷。”一位AR行业创始人表示。
定价策略也引发质疑。带显示功能的meta Ray-Ban Display起售价799美元(约合人民币5676元),远高于国内同类产品如Rokid Glasses的3299元。高昂的价格可能将其限制在极客尝鲜群体,难以触达大众市场。相比之下,第一代Ray-Ban meta眼镜的成功更依赖生态绑定而非技术参数。2023年9月发布的这款产品,通过与Instagram深度整合,实现第一视角拍摄并直接分享至平台,2024年全球销量突破100万副,今年同比增长超300%。其核心逻辑是:用户用眼镜拍摄独特内容,获得更多关注与流量分成,从而将设备从“科技玩具”转化为“生产力工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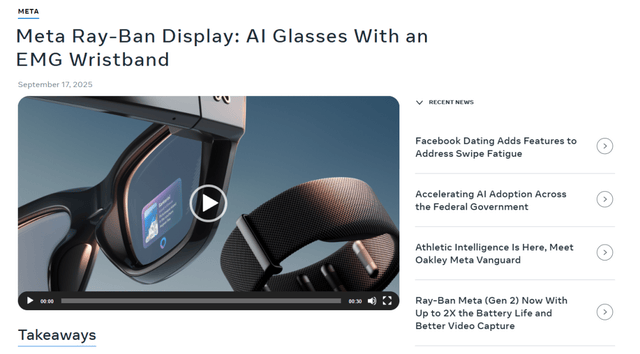
但新一代产品似乎迷失了方向。发布会演示中,AI在回答“如何调制韩式牛排酱”时反复给出重复答案,最终因无法处理追问而中断;扎克伯格尝试接听视频电话时,屏幕未显示接听按钮导致失败。这些场景暴露了产品交互与硬件协同的不足。更关键的是,meta为追求显示、腕带等“科技属性”,可能偏离了第一代产品成功的本质——作为时尚单品与内容创作工具的简洁性。
meta的焦虑背后,是元宇宙概念破灭后的战略转型。扎克伯格将AI视为避免被时代抛弃的关键,宣称要“创造比人类更聪明的通用人工智能系统(AGI)”,并在硅谷掀起天价挖人潮。但急于证明自己的心态,让新款眼镜搭载了太多尚不成熟的技术。当创始人自己都无法流畅演示核心功能时,用户自然不愿为“半成品”买单。一位科技分析师评论:“meta的问题不是技术不够,而是太想用技术证明自己,反而忽略了用户真正需要的到底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