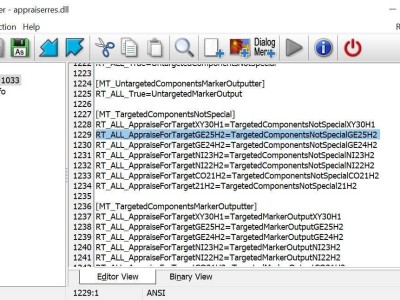在春意盎然的季节里,万物都迎来了生长的最佳时机,人类幼崽的身高问题也成为了众多家庭关注的焦点。在这个科学至上的时代,孩子的身高似乎也应该遵循某种可预测的生长规律。
一个广为人知的预测方法是,根据父母的身高来推算孩子未来的身高范围。例如,男孩的身高预测公式为:(父亲身高+母亲身高+13厘米)÷ 2±7.5厘米。其中,前半部分被称为“遗传靶身高”,是先天决定的身高基础;而后半部分的“±7.5厘米”,则代表了通过后天努力可能改变的身高范围。
梁宇,一位在药企从事研发工作的母亲,对女儿的身高问题尤为关注。她和丈夫的身高都不出众,因此对女儿萱萱的未来身高并没有过高的期望。然而,当萱萱进入大班后,梁宇还是决定采取行动,为女儿报了跳绳兴趣班,希望通过运动、光照和补充维生素D等科学方法来促进她的身高增长。
几年的努力下来,萱萱在跳绳比赛中获得了奖项,但身高增长却始终保持在每年5厘米左右,远低于同龄孩子的平均增长水平。更令梁宇担忧的是,萱萱在三、四年级时出现了早发性发育的征兆。性激素和生长激素是影响孩子身高的两个关键因素,早发性发育可能导致生长期缩短,从而影响身高。
面对这一挑战,梁宇带着萱萱去了医院,经过一系列检查,医生建议使用能够抑制早发的“达菲林”和助长的生长激素。重组人生长激素是一种经过国家药监部门认证的药物,可用于治疗儿童生长缓慢。从1950年代开始,学者就成功合成了人生长激素,并逐渐应用于临床。如今,这类药物已获批治疗多种适应症,成为许多家长心中的“增高神器”。
市面上常见的生长激素有粉剂、短效水剂和长效水剂三种类型,主要区别在于注射频次和价格。梁宇为萱萱选择了昂贵的进口生长激素,但随着治疗时间的推移,花费也迅速攀升。尽管如此,看到女儿身高有所增长,梁宇还是感到了一丝欣慰。

上海和睦家医院的儿科医生王秀民接诊了许多像萱萱这样的孩子。她发现,近年来咨询身高问题的家长越来越多,甚至有的孩子才两三岁就被带到了诊室。这些孩子中,很多并不符合生长激素的标准适用群体。然而,在现代社会中,身高对孩子的心理健康、未来恋爱和求职等方面的影响不容忽视。因此,医生们会在符合基本指征的情况下,有意识地放宽注射标准。
然而,即使放宽了几厘米的注射标准,仍然无法满足一些家长的期望。在身高问题上,“及格”远远不是标准,超出平均值也只能算是“达到预期”。许多家长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在人群中脱颖而出,成为高挑挺拔的那一个。因此,一些身高已经处于中等水平的孩子也被带到了诊室,希望通过生长激素来实现更高的身高。
王秀民医生对追高家庭的印象是“动作上身体力行,金钱上不计成本”。她提到,一个流传在医生之间的玩笑话是:“你想长多高,就把人民币在脚下垫多高”。尤其是在生长发育期这个黄金窗口期里,时间等不起。一旦骨骺闭合,身高增长就会停止。
大学生阿琳见证了弟弟一路追高的历程。弟弟在3岁时被确诊为努南综合症,一种罕见的基因疾病,也是生长激素治疗的适应症之一。如果不打针,预测的成年身高只有130厘米左右。这个身高对于阿琳一家来说是无法接受的。因此,从那时起,弟弟就开始了漫长的追高之路。全家人时刻准备着为他提供良好的营养和运动环境,以及冷藏保存药物所需的装备。如今,弟弟已经13岁,身高基本与同龄人持平,但每日与生长激素相伴的日子已经成为了他生活的一部分。
尽管生长激素在帮助许多孩子实现身高增长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外界对这种外源注射方法的质疑声从未停息。副作用、安全性等问题一直是家长们关注的焦点。因此,一些非药用“追高”产品也逐渐崭露头角。这些产品如膳食补充剂、益生菌助长产品等,虽然缺乏真实临床数据支撑,但仍然吸引了众多家长的关注。
然而,对于已经占据高市场份额的国产生长激素厂商而言,最大的业绩变量来自于“集采”。近年来,针对生长激素多种剂型的省级联盟集采陆续展开,导致粉针剂型等“基础款”的利润被严重压缩。生长激素的高毛利时代由此开始走向下坡路。但对于依然广泛的“追高”家庭而言,这或许意味着更多的选择和更合理的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