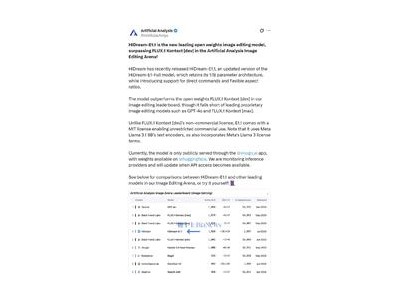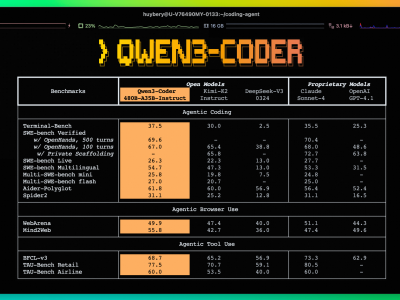英伟达在全球科技舞台上的强势表现,让其创始人黄仁勋一度被视为没有真正敌人的行业巨擘,特别是在其公司市值突破4万亿美元大关,登顶全球市值榜首之时。访华期间,黄仁勋对中国汽车企业的广泛赞誉更是成为网络热点,引发业界热议。
然而,在这光芒四射的景象之下,却隐藏着一些不为人知的暗流。那些曾被黄仁勋公开赞赏的汽车企业,正悄然寻求与英伟达保持距离。
“相当可怕。”这是通用汽车内部对英伟达辅助驾驶方案的评价。今年3月,黄仁勋亲自宣布了与通用的合作,计划基于英伟达技术打造自动驾驶车队。他还展示了英伟达在汽车领域的雄心壮志,包括与丰田、奔驰等企业的合作,并预计2026年自动驾驶业务将带来50亿美元的收入。然而,本月初的评审结果却给这一合作蒙上了阴影,据知情人士透露,英伟达自动驾驶团队已将这一结果告知了黄仁勋。
这并非英伟达在汽车创新业务上首次遭遇挫折。在此之前,奔驰也曾给出过类似的负面评价。去年6月,奔驰CEO康林松及其技术副总裁在美国进行了长达上千公里的跨城测试,对比了搭载英伟达和Momenta辅助驾驶系统的车辆。结果令人震惊,即使在英伟达的大本营北美,其辅助驾驶效果也不如中国的初创公司Momenta。
这一结果让英伟达汽车业务负责人吴新宙感到不满,特别是考虑到Momenta的软件仅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调试。据透露,奔驰已经将中国区多款车型的辅助驾驶业务从英伟达转交给了Momenta。而英伟达的另一个软件客户捷豹路虎也在寻找新的辅助驾驶供应商,甚至有消息称,英伟达员工在中国已基本不再对接车企项目。
在中国这个竞争激烈的汽车市场中,车企没有多余的时间等待英伟达。尽管汽车智能软件业务对英伟达来说只是其庞大业务版图中的一小部分,即使加上汽车计算芯片业务,这部分收入在英伟达1305亿美元的整体收入中也仅占不到2%。然而,这看似微不足道的业务却承载着英伟达对未来人工智能走进物理世界的重要布局。
智能汽车被视为最先落地的具身智能产品,其产业基础成熟,使用场景标准。因此,拥抱汽车自动驾驶几乎等同于拥抱物理世界的人工智能。英伟达已经预见到这一点,将汽车和机器人部门合并,并相信未来小米、比亚迪等企业都能造出优秀的机器人。
然而,尽管车企过去一直追逐英伟达的首发芯片,但从最新一代的Thor雷神芯片开始,英伟达在中国市场正面临失去头部客户的风险。这一威胁不仅来自专注于辅助驾驶业务的华为、地平线和Momenta,还来自中国新造车公司的自研芯片努力。
蔚来、小鹏等企业已经推出了自研的车载AI芯片,理想汽车的辅助驾驶芯片也计划明年量产,小米创始人雷军也明确表示将很快推出自家的汽车芯片。然而,推出芯片的难度巨大,中国车企和服务商面前堆叠着海量的挑战。
英伟达新款Thor芯片的延期风波就是其中之一。去年底,理想汽车因英伟达Thor芯片未能及时交付,将增程L系列改款车型的上市时间从今年3月推迟到了5月。这一变动导致理想汽车月销量损失超过万辆,对应约60亿元的销售收入。而小鹏汽车在看到Thor延期风险后,果断搁置了Thor平台的开发,集中资源紧急适配自研的图灵芯片。
车企们原本担忧自研芯片成熟度不足,但在对比英伟达Thor上车的艰难体验后,他们开始释怀。据透露,英伟达最早交付的Thor芯片存在大量工程和设计问题,算力也无法达到官方宣传的700TOPS。双方经过数轮调整后,才达到量产交付效果,但目前可释放的算力仅在500左右。
面对这一困境,理想汽车已经加快自研芯片的上车进度,计划在明年一季度交付上车。而蔚来、小鹏、比亚迪、小米等企业也都将推出自研汽车芯片。多位车企管理层表示,长远来看,英伟达芯片可能只在海外车型中有需求。
过去四年,中国头部车企在自研芯片上可谓卧薪尝胆。踩坑是常态,不仅要花费大量资金购买IP授权和EDA等工具,还要面对芯片链条上技术公司的合作难题。小鹏汽车的图灵芯片项目就曾大幅度调整设计方案,并向早期合作方赔付了巨额赔偿金。
蔚来的自研芯片之路也充满惊险。在芯片前端设计即将完成的关键时刻,一家重要的合作伙伴突然决定结束中国区业务。蔚来不得不自己搭建后端设计团队,去台积电申请账号,一步步推进到流片。尽管困难重重,但车企们对自研芯片的热情不减。
车企自研自动驾驶芯片的核心价值之一是降本。搭载自研芯片后,整车成本可以降低数千元至数万元不等。然而,更长远的战略价值在于算法和芯片的高度匹配。小鹏汽车的整个AI技术栈都在围绕图灵芯片设计,包括正在开发中的基座模型。而理想汽车也在积极探索大模型技术在汽车上的应用,认为自研芯片可以更快地反馈和调整算法问题。
然而,英伟达似乎并未按照车企的节奏走。在销量为生命线的汽车市场中,交付是车企和供应商的头号使命。但英伟达在强交付体系上显然未能满足车企的需求。Thor芯片面向整个机器人领域,并非专为汽车而生。它基于英伟达最新一代的AI芯片架构Blackwell设计,而Blackwell架构的GPU则采用台积电N4P工艺制造,这并非专门为汽车芯片而生。
车规级工艺意味着更严苛的安全标准,包括晶圆厂、封装和测试等环节都要符合车规要求。这无形中推延了Thor的交付时间。一款产品的延期几乎导致汽车客户百亿级的损失,这在任何汽车供应链公司都会引发反思风暴。但在英伟达内部,这似乎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
因为英伟达并非一家汽车供应链公司,汽车业务在其版图中占比不到2%。英伟达考虑的是如何攻克技术难题,想的是远方,而不是汽车交付的当下。如果以当下交付的节奏优先,汽车芯片其实可以用更成熟的制程实现。但在资源配置上,英伟达也未向车企倾斜。
多位车企工程师表示,在面对Thor交付困境时,能看到配置的资源确实不足。而黄仁勋在日常工作中也很少过问汽车业务。服务车企不在英伟达的优先级排序前列,这跟同样强势的顶尖车企形成了难以调和的矛盾。
在芯片之外,英伟达想要发力的自动驾驶软件领域也面临着中国技术公司的围追堵截。在自动驾驶软件算法上,硬件出身的英伟达曾与软件起家的创业公司Momenta多次交锋,都处于劣势。尽管英伟达汽车业务负责人吴新宙曾带领团队驻扎上海进行开发,但与Momenta的体验仍有差距。
企业文化是一道巨大的沟壑。加入英伟达后,吴新宙虽然在中国招募了团队,但英伟达辅助驾驶团队的主力都在美国,中国团队几乎无法做决策。而国内头部玩家要么团队规模庞大,要么高强度封闭式开发,交付和执行力都更能满足国内汽车客户的需求。
英伟达正在试图激发团队活力,但面对中国企业的激烈竞争,英伟达在汽车领域的护城河似乎并不稳固。不少合作车企都在观望,英伟达的汽车芯片或软件业务是否会被放弃。而机器人市场或许是个长期的战场,但第一场战役已经在智能汽车这块最佳试验田中打响。